推石头的人
在最赚钱的那类游戏中,有一类没有终点的游戏,通称为内容向“服务型游戏”。这些游戏需要周期性地为庞大的用户群体提供内容,从一个版本到另外一个版本,在整个生命周期中,它们要永远根据用户的需求来推出更新,直到死亡。
在现在,内容向的服务型游戏们正趋于零和博弈,与之对应的是,用户对内容的要求也水涨船高。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这些了。但很少有人关心,为了满足用户无尽的内容需求,这些游戏的生产者们正在经历什么。
为了支撑起周期性的版本内容,他们就像寓言中的西西弗斯——如果说一个版本是一块石头,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周期内把石头推上山,然后迎来下一个周期,如此循环。这一套循环最大的问题是,给他们带来痛苦的,不仅是推石头这个动作,还包括石头本身,包括那座山,甚至是设定这个规则的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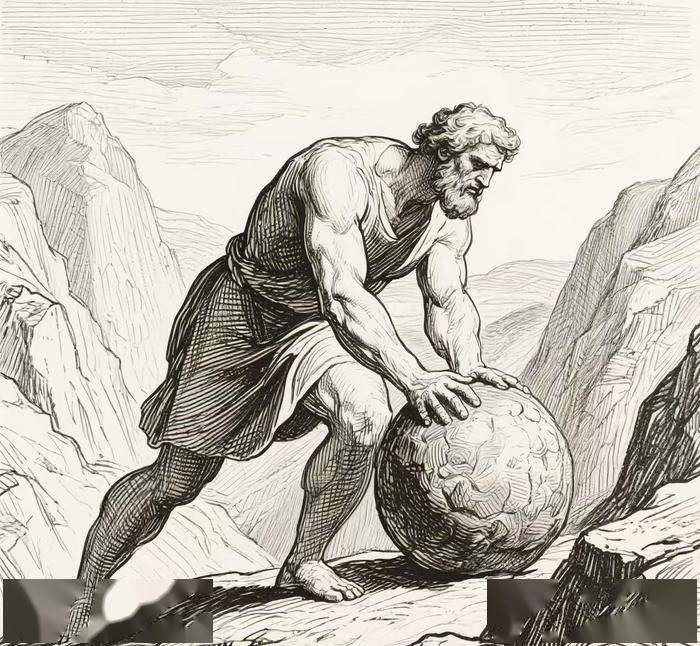
有很多人把自己比作推石头的西西弗斯
“周期性版本更新非常狗屎……我们特别卷,每个版本得有新活儿,玩家才会觉得好。代价就是,我们在一个完整周期内,要做的工作量是呈指数级上升的。”——某头部项目策划
“周期性版本更新是有原罪的,这种原罪又会在市场竞争和高自我要求中被放大。”
依文熬到凌晨下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他目前在一家头部厂商的一款知名二游项目做策划。这是他加班最狠的一段日子,“虽然上一个版本的人也加,但没天天加到这个点儿的”。
依文觉得,加班是由两方面问题导致的。一是周期性版本更新模式。服务型游戏的本质是持续服务社群,“内容向”更是要通过沉浸式的视听、剧情叙事等留住用户,而内容本身是会被消耗的,玩家会觉得不新鲜。
被消耗的不仅是创意,还包括创意的表现形式。这就给所有人提出了挑战:“我们每个版本是不是得有新活儿?有新活儿,玩家才会觉得‘卧槽,这是史诗更新’。”
然而,版本的周期是固定的。“有新活儿”意味着开发团队成员要在固定的周期内做出越来越高质量的内容,大多数情况下,厂商需要压榨人力才能完成这个目标。“你想,我们要怎样才能同时满足新内容的质量和周期呢?答案是继续压榨当前版本的人力,这等于说是向后面版本的排期贷款……以贷养贷。”
依文举了个例子:“比如一个大版本周期1年半,小版本周期1年,说是这么说,但最后到落地环节,尤其关卡和任务这里,就俩月不到。全配进去还得正确,还得接受过程中各方拷打,比如验收时觉得内容效果不行,要改设计,美术觉得能做完就不错了,我们改个锤子;程序觉得时间不够了,要新功能也没得加,只能委屈委屈策划……”
在艰苦的拉扯和苦难行军式的开发中,依文发现自己在每个周期内要做的工作量是“呈指数级上升”的。新周期比前一个周期工作量多,甚至周期的时间也不一定固定,“小版本内,开发时间还会压缩”。这些原因加起来,导致了他一个多月的超长加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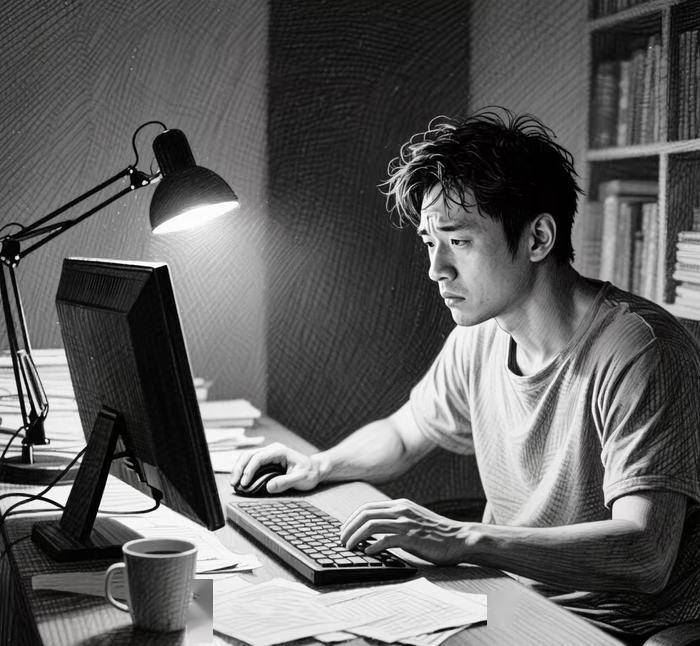
依文发现,自己的工作量在逐渐上升
与市场上的其他游戏比,目前的项目要求较高,是依文这段时间加班到凌晨的第二个原因。“有的项目聪明一点,它挤牙膏,不会要求每个版本搞什么太大的活儿,常规内容一直铺,少量整新活儿,而且集中在角色上。玩家骂归骂,但每个版本的内容相对可控。”然而,依文所在的项目要求每个版本要有又好又足量的新内容。“每个版本都要卷,”他说,“卷的都是一线研发的命。”
刘东对此也深有感触,他是资深从业者,曾在某个知名项目担任文案。那个项目对质量有极高要求,作为文案,他要在极短的周期内凑出剧本。他要面向的群体不仅有用户,还有组内的高追求,这导致了极致的压力。“只要在那个项目组里干了超过2个版本,就是老人了,属于经验丰富,因为绝大多数人只能扛1个版本。”刘东说。
而从时间上来看,几个版本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。
“操作权在谁的手上很重要,对那些有创作权的人,他的痛苦是一种长期的痛。”——某项目资深文案
对一些人来说,无法做自己想要的内容是一种痛苦,但对于能决定做什么内容的人来说,他们遭受的又是另外一种痛苦。
邓聪已经快20个小时没睡觉了。原因很简单,睡不着。他只要一闭眼就会想起自己的工作,最近1个月,他去了几次医院,靠买安眠药来帮助入睡。
他是一个项目的资深研发,他的压力来自于越来越无法把握内容要怎么做。他无法对产出内容的好坏做出直观的评估,只能依赖数据反馈。
“我们努力做内容、给用户构建一个特别的世界时,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:首先,我们无法找到一套固定的生产模式,而用户只会要求越来越多的新鲜感。我们无法从一片内容海中,挑出用户喜欢的内容。” 他对触乐说。
服务型游戏面向用户,每个版本更新的内容好不好,用户当然有决定权——直白点说,用户喜欢的内容才能被称为“好内容”。但邓聪焦虑的是,经过验证,他们发现“让用户觉得好”的只有“新内容”。“新内容要经过(用户)检验才能知道,但经过检验的内容又不新了……调研没用,简直是个死循环。”
“市场上,这个版本的内容好,用户就认你,下个本版的内容不好,用户就不认了。”邓聪觉得还是那个原因——市场要求每个版本的内容都要比上个版本更好,但生产者的能力是有极限的,到了极限后,就只能“卡在一个靠玄学的位置,进步空间无从摸索”。
而且,邓聪觉得,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,有时候东西做不出来,就是做不出来。“我之前踩着时间点做出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角色,但并不意味着我下次还能做出来。” 然而负责验收的上层并不会一直理解他,“原则上他能理解,但在执行上,他会埋怨你,觉得你不够努力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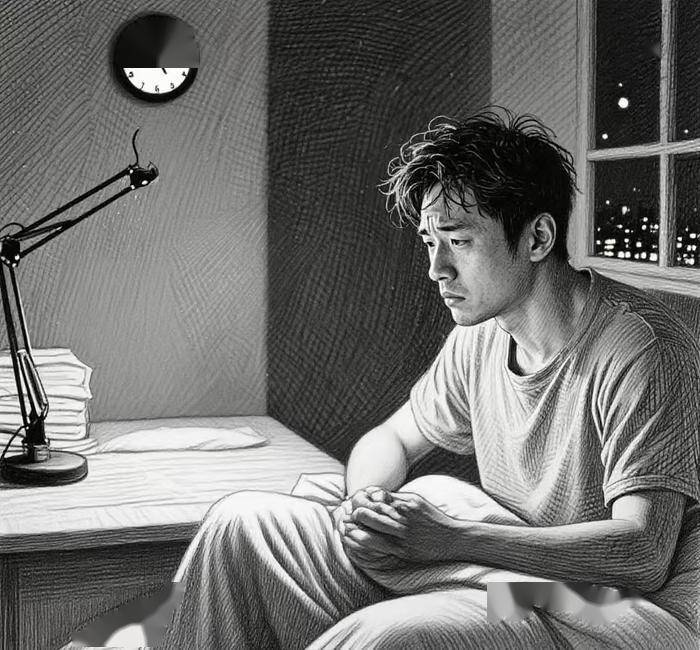
失眠是一些创作者的常态
很多项目会把版本更新周期的“时间节点”排在一个团队产能极限的位置,这导致所有创作者长时间处于疲惫之中。“只有在内容型游戏里做过,你才会知道赶版本这个事儿有多累。”邓聪向我描述,最近1个月,因为赶版本,整个办公室里的文案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房间。大部分人半夜12点才会下班,有些人甚至会调休,让自己昼夜颠倒,晚上8点,人都走完了以后才开始写,“白天办公室太吵,根本写不了”。
“很多需要跨部门协作的事儿,理论上应该提前沟通。但对面没有意识,他就不跟你讲。你给他反馈了,他又不开心。”——某项目资深研发
内容生产流程中,总是有损耗的,这种损耗往往也给许多从业者带来了痛苦。
“无尽的加班、无尽的折磨,还要扯皮,要为别人的问题买单,这是最痛苦的时候,而且这种痛苦循环个不停。”这是刘东最近的感受。在他看来,最大的压力不仅来自于赶版本时的加班,更来自沟通。
随着游戏规模越来越大,越来越复杂,投入开发的人员和部门就会越来越多。跨部门协作是游戏生产中必然遭遇的事情。很多公司都会搭建尽量合理、高效的管线,但人的问题始终存在,耗损也始终存在,也始终在给生产者造成精神压力,因为内容生产“不可能是纯靠逻辑和理性驱动的流程,一定会充斥着大量的拉扯、扯皮、甩锅”。
这也导致内容生产的效率实际上不完全取决于团队规模,而是取决于极为全能的“骨干型员工”的数量和状态,这类核心员工数量多、状态好,那么内容产出就会相对顺利,反之,大型项目虽然人多,但效率不一定会高起来。
黄石就是其他人眼里的“骨干型员工”。他在一家知名二游项目中担任管理职位,不需要亲自参与内容生产过程,日常更多是把控内容的方向和流程。从他的视角来看,现在许多项目是“躺在地上,等着神仙来救”,每个项目的老板都“希望有一个能有框架,能执行,能教教大家怎么写的人来带着团队创造内容”。这本质上还是因为内容市场难做。对于他这个级别的人来说,压力“不仅限于实际的开发,还包括了周围人的期待”。
黄石认为,会出现这一局面,核心原因还是用户对内容的需求越来越高,而内容生产者的能力越来难以满足需求,版本周期的限制又强化了这一点,“我的诉求很基础,能达到设计预期的80%,活下来就行了。真的不追求什么高大上,保证团队的团结是最重要的”。
刘东则觉得,很多无效的扯皮在于团队规模过大,跨部门协作需求很高,但“跨部门协作后的产出的验收标准又非常模糊,内容终究是较为感性的,不像别的品类那样有完整的数据支持”。
大部分项目的标准是最直观的流水。设计者们会依据每个版本的收入变化来评估整体内容的导向,但每一个版本获得的是用户整体性的反馈,内容开发时则要拆成一个个模块来进行——“各个部门在围绕一些基于直觉的设计扯皮时,会发现争论的东西没有标准,不能分清谁对谁错,最后一地鸡毛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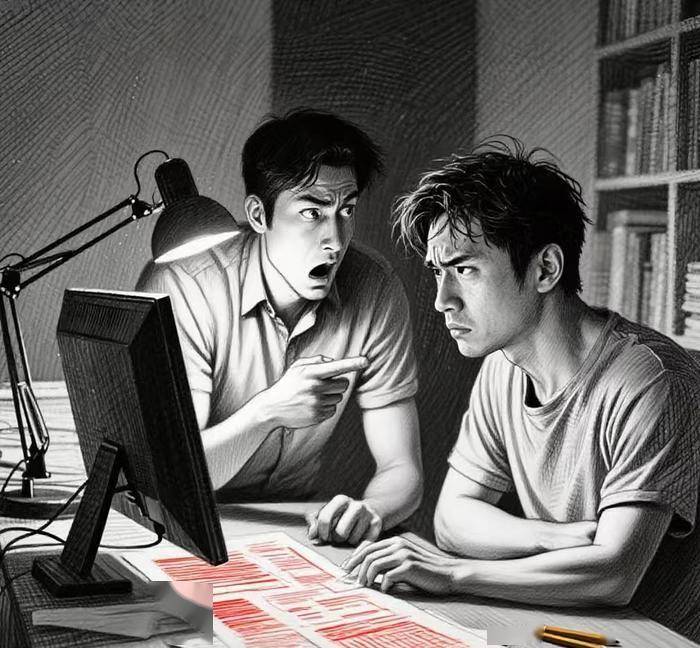
开发中常见跨部门扯皮,让人感到十分疲倦
与此同时,所有的人又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巨大的版本压力。在这种压力下,人经常会出错,然后每个人都可能会为别人的错误买单。
有一次,时间压力很大的时候,刘东接到了美术提交的某个素材,由于美术并没有在设计时跟他预先沟通,素材跟他想象的不一样。“美术没有走流程的意识,自己做完了之后扔到群里来,导致我不能直接跟美术说这个不行,只能说我们现在只有半天时间,能不能简单改一下。我还要帮他想办法,你这个往什么方向改,能做到又快又好。”
这个例子很小,也并不严重,却需要让刘东和美术都加班解决,“我还不能跟美术说(你没走流程),因为人家愿意给我改,我只能说一起想办法,但这个事儿,理论上我们应该提前沟通。”
“(新人)干个三五年就30岁了,30岁没干出爆款,基本上就这样了。”——某知名项目内容负责人
在服务型游戏的内容工厂里,无论是生产者,还是生产管理者,除了内容生产压力外,还要面对一种焦虑,它来自于外部大环境,又与服务型游戏这个品类的特性紧密相连。
作为领导层,黄石不用像项目组里大部分人一样加班到凌晨,但他仍然遭受着极大的精神内耗。这种内耗是大环境带来的。
“我们无法像欧洲那样形成自己的手工业作坊,20年前在做这个品类,20年后还在做这个品类,不是说有多坚定,而是他们可以这样活下来。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快乐,但这两点在我们这里都是跑不通的。”
黄石把服务型游戏形容为“在一块追求完全胜利的赛道上厮杀”,市场变化特别快,项目一旦成功,带来的收益也特别巨大。在这种不确定性强、机遇又很多的环境里,公司内部氛围就必然趋向“社达”。“哪怕不参与其中,你也要天天看着同僚跟你说‘哎,这个公司随便一个资深,一年就能拿100多万,躺着不用干活’或者‘那个制作人一年拿2千万’,成天听这些话,很难不焦虑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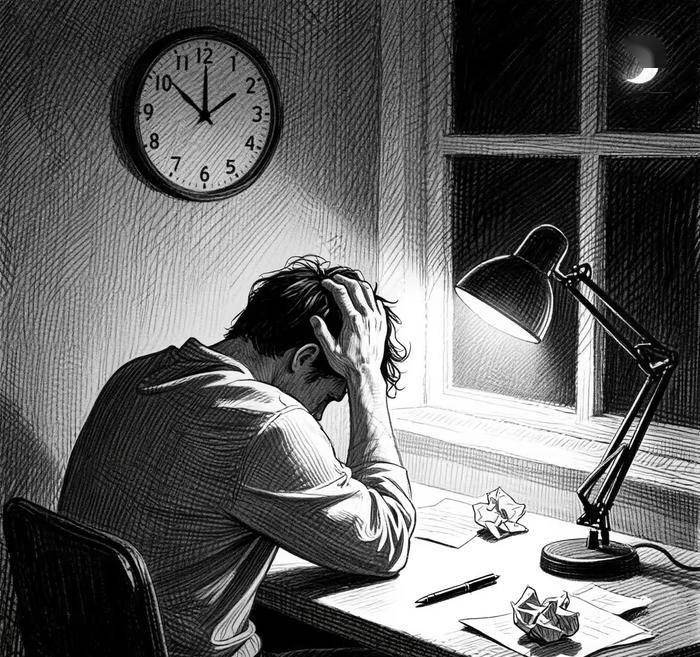
焦虑弥漫在厂商内部
在这种环境下,人会容易焦虑自己的成就。“每天看到别人赢了,然后自己没赢,你会很焦虑”。这种成就又包含了“名”和“利”——黄石目前所在的公司有一个知名项目,产出内容在玩家和业内的口碑一流,盈利能力也很强,但一线工作者拿到的薪资只有中上水准。原因在于,项目人员会默认薪资构成中包含了这个项目的“名”。
“名”意味着能爬到更高的平台。在某个地方,当薪资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,精神焦虑就会成为那儿的普遍现象。
“你人生中最巅峰时期不过3到5年,他们会把它拿过来,让你加入这个团队。等年纪大一点了,他们觉得你不行时,又把你踢掉。”——某知名项目研发
内容生产者的焦虑不仅来自于大环境,也来自他们对个人职业发展的预期。
吕峰是2024年的毕业生,本硕连读7年出来,现在25岁了。他非常幸运,进入了一家头部厂商的一线项目。但即便如此,他对未来依旧充满焦虑:“现在项目组基本只要能力对口、领域垂直的人了,越快上手越好,我虽然进了这个项目,但我从这儿学到的那些垂直的东西,真的很难带到下一个周期去。”我问他,“周期”的意思是什么,他答:“比如说我现在做二次元,但我无法保证3年之后,二次元游戏还是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吕峰对整个二次元品类的发展持较为悲观的态度:“你去看看,现在市面上其他几个二次元头部公司,都已经不做二次元,他们的新项目没有一款二游”。他很清楚,公司上层想要转方向是没有太多成本的,支付成本的只能是一线研发。
其他游戏品类也有类似的情况,但这一点在内容向服务型游戏领域更加让人担心。每一类游戏都有自己的细分人群,有自己的设计特性,有完全不互通的经验和技术。吕峰觉得,自己做二游时积累的经验在别的品类完全不能用。
那跳槽或者转品类呢?吕峰已隐隐知道,行业内还存在一个叫“嫡系文化”的东西。“这意味着,如果你是社招进去的,你很难成为嫡系,只有校招生才能被培养、被认作‘自己人’。如果无法成为嫡系,很多项目是没你份的。”
吕峰向我举了一个例子——某知名项目的一位资深文案,34岁时被原来的项目开掉了。他本来调去了公司的一个新项目,结果那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从另外一家厂商跳来的,他被对方认为“不是自己人”,最后被排挤走,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。
吕峰觉得自己又清醒又痛苦:“我们现在都是做长线运营游戏,这里有个最现实的问题,就是每个版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推石头?因为每个版本的资源是一样的——我做得好与不好,跟我有什么关系?3年到期,如果不是嫡系,那就再见了,利用价值用完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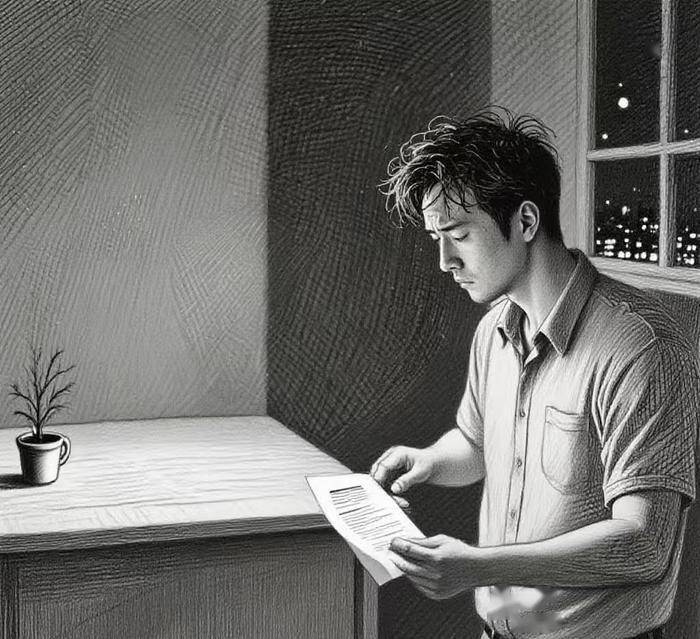
个人的未来发展,也让从业者焦虑
3×6=?
摆在西西弗斯面前的永远是一座高山、一颗岩石和一件永远干不完的工作。这就是内容向服务型游戏开发者们的处境。
西西弗斯是神话角色,但内容生产者们终归是人。人是有状态的,人需要休息,会被其他事情影响,只有状态好的时候才能极限操作。连续推动3个月、5个月的石头,动作终归会变形。
然而他们需要一直推石头,市场是不会停下来的。这当然可以说是游戏向“工业化”发展导致的结果,当我们津津乐道于管线、效率或更全面的内容时,有些人在为此付出代价。这些人几乎得不到应该属于创作者的乐趣,对于他们来说,创作可能已经成了负担。
然而没有任何人有办法,也没有人能改变这些。我们没法回到过去,竞争开始后就不会停下了。这并不是一个人,或者几个人的问题,也并不仅是游戏行业面临的问题。所有内容生产行业在当前这个时代都面临这样的问题——人们需要更大量、更精美和更刺激的内容,随时都要;消费内容的人看不到内容生产者,他们只能看到石头被推到山顶的那一刻,为那一刻欢欣鼓舞。
业内流传着一道乘法题:“如果说一个团队的人力极限是3,每个版本的周期是6。3乘以6就是这个团队在这个周期的内容产出能力。假设我们需要依据这个数字来制定团队的工作目标,那么这个数字是多少?“
答案是:没人会在乎 。
(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。题图、插图由AI创作,内容与本文无关。)
